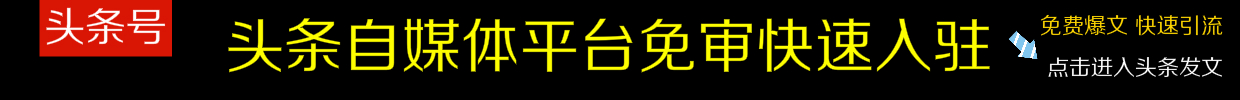賀 疆
在動筆寫這本《肖像背后的帝王志》的那天,我坐在陽臺上,看了一天的云,從朝暉到晚霞,日光繞著我,把我的身影拉長,縮短,又拉長,窗外的空地上孩子們在放風箏。當我給這本書畫上句號時,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兩年了。
歷史是由一個個時代連接而成,每一個時代的印痕又是由一個個事件疊加而成,而每一個事件背后都是一個個鮮活的人。了解歷史,除了史家那一支筆外,最直接最形象的莫過于肖像畫,看著那在時間的迎來送往中依舊散發著生命氣息的畫作,原來肖像是光影的印痕,就這樣給歷史鐫了刻度。線性的時間,面狀的空間,點狀的人物,歷史就是這樣構成的吧。
那些帝王像一幀幀掠過,當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,曲未散盡世已非。矚目那一個個尊貴無匹的人物,通過那一幅幅畫布,看盡縱橫捭闔、刀光劍影、金戈鐵馬、鼓角錚鳴;賞罷閑情逸致、云煙蒸騰、波詭云譎、悲歡離合。山高水長的歷史,起起落落不外乎生命的疊進,以及生命帶給我們的哲思。

《依舊西窗月——肖像背后的帝王志》賀疆著 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
如是,就以時間的視角走進歷史,梳理一下帝王肖像背后的悲歡離合。不厚此薄彼,也不等量齊觀,只做一個隔代的知音,與他們做時空的對話,說他們的沉浮故事,聊他們與時代的互動,談他們與歷史的關聯。
肖像,即寫真,是真實的再現。在繪畫史上,肖像畫是發展較早的繪畫種類。在沒有照相機、錄像機的時代,寫真肖像是留住光陰最好的手段。真正的肖像畫始于14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,達·芬奇的《蒙娜麗莎》就是個中經典。16世紀,提香、丟勒、萊奧納多、荷爾拜因等在人物繪畫方面的成就已經很高。到了17世紀,肖像畫發展到巔峰。這一時期,最著名的當是凡·代克。時間,把畫家的畫技淬煉得爐火純青。
而肖像,除了對個體的關注,希望留駐時光之外,更具有廣泛的社會功能,比如政治宣傳、政治聯姻、國際邦交、圖像報告、彰顯身份等,尤其涉及皇家時,肖像畫的職能遠不是滿足自我內心需要那么簡單。
在這些畫作里,很多成了紀念碑式的作品,比如丟勒的《查理五世像》、凡·代克的《查理一世行獵圖》、大衛的《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拿破侖》等;有的是生活片段的記錄,比如門采爾的《腓特烈大帝的長笛演奏會》、委拉斯貴支的《宮娥》等;有的是歷史事件的承載,比如約翰·菲利普的《國民軍》等,不一而足。
而作為交流紐帶和橋梁角色的是藝術家,他們擔負的是信息的傳達,一幅優秀的肖像往往勝過千言萬語。這總令人想起中國歷史上王昭君和畫師毛延壽的故事。大多數的肖像畫家,是比較尊重真相的,盡管也會做技巧性的彌補加以美化和粉飾,比如丟勒在《查理五世像》中,胡子遮蓋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下巴,而且,彼時年邁的查理五世已經無法騎馬,在戰場上是在馬車上指揮戰斗的。大衛在《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拿破侖》把拿破侖描繪得威風凜凜,但實際上跨越山峰時,拿破侖是牽著騾子艱難行進的。但這都不影響畫作傳達出來的撼人心魄的英雄氣概,這種藝術的真實,恰恰往往符合人們心底的期許和密望。在真人真實寫照這方面,只有戈雅做到了,他把《卡洛斯四世一家》真實地呈現在畫面上,竟然讓刁鉆刻薄的王后默然接受而沒有發難,倒真是奇跡。
時間如洪流,多少豐功偉業、多少風云人物,都做了塵歸了土,留下的是世間流轉的故事和那些永不褪色的藝術。故事可以戲說可以演繹,但藝術卻是觸手可及的真實。常常看著那些畫作里的人物,會生起好奇的心,想一探究竟,更想穿越進他那個時代,親歷那一朝風土人情、那一代文化氣息,以及那一番生死博弈。也好奇作畫的人,怎么可以用一支筆輕輕松松地就框定了一個人生、定格了一個時代。大概,這就是藝術的魅力,經典的力量吧。
寫這本書的時候,常常看著這些畫作,會感動,入心的感動。也常常寫一個人物,寫著寫著把自己寫哭了。讀畫,讀出心靈的共鳴,用藝術的視角體會,竟是一種全新的洞察。原來,那畫作,凝集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;原來,那畫筆如刀,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刻痕;原來,那歷史的拐點,竟然是一重又一重的輪回上演。

《記得那年同坐》《依舊西窗月》《今朝風日好》賀疆著 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
實話講,中學學世界歷史時,經常會頭疼,為那煩瑣冗長的名字,為那祖孫不分反復使用的名字。但是,自從踏入美術界,學習西方美術史時,其實也并沒有真正把美術和政治意義上的歷史關系搞清楚。我常常氣餒,是書籍沒說清楚,還是我自己迷糊。經常是搞清楚了某某畫派,但對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帝王政治又勾連不上,真是糾結不已。我就一直想,該有怎樣的一個切入口,可以讓藝術、藝術史和政治歷史結合起來。
這時,肖像畫進入我的視野。歐洲各國皇家流行肖像寫真,歷代如此,且迥異于中國古代帝王像的千篇一律。這一特殊現象,讓我意識到在汗牛充棟的美術資料里,把藝術、藝術史和政治史結合起來,這恰恰是一個空白。于是,我以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為經貫穿始終,以歐洲各國君王之間的橫向聯系為緯做時代宏闊的描寫,縱橫兩條線索構成坐標軸,而交集點就是一個個帝王。這樣既交代清楚了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背景,也讓人物在錯綜復雜的關聯中特征鮮明。一幅肖像畫作,除了前文所述的功能之外,在本書中承載更多的是歷史功能,它們就像一個個時間之尺上的刻度,清晰地標明歷史的軌跡。

作者簡介:賀疆,女,祖籍河北。美術史論家、作家、藝術策展人。樹一家之言:創后未來主義和后水墨兩大理論,填補了美術史空白。后未來主義為中國藝術走向提出宏觀架構 ; 后水墨理論為中國當代水墨做劃時代的書寫,為中國水墨發展方向提供可參考方案,并鮮明提出殖民水墨和后水墨兩個學術概念。 開散文化評論先河,文筆清新優美又不失犀利,兼具傳統文化之美。著有《批評的人生·批評家素描》《對面》《記得那年同坐》《依舊西窗月》 《今朝風日好》《禪茶問道》等。策劃主持《后未來主義》和《后水墨時代》等系列學術主題展,并策劃主持有大中型群展及個展。
點、線、面構成畫作,也構成歷史。以時間為線,以時代為維,以人物為點,一個個歷史的斷層,一個個時代的橫截面,就這樣清晰起來。本著情懷,填補美術史的空白,這也是本書的價值和意義。當然,在本書中,也把畫作的作者做了介紹,賞畫、讀史、讀人,是它應盡之責。
觸摸藝術,遙望往昔,原來歷史的高貴和深邃,一直在里面。
“天地者,萬物之逆旅;光陰者,百代之過客。”在收筆這一天,窗外的藍天白云一如起筆那日的云卷云舒,遂想起李白這一句詩。原來,天地間只有逆旅和過客。
原本來,世間一切,終究抵不過時間。恰如那一輪西窗月,照盡千秋歲月,月華如舊。
2019年2月9日 于上林別苑